首页>秀风采秀风采
“四有”教师童庆炳
童庆炳
【写在前面的话】
一篇迟到的通讯
2013年春节后,我因为一个小问题去采访童庆炳先生。去之前,我就知道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文艺学泰斗,曾培养出罗钢、王一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当今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皆出自其门下,所编文艺学教材被500多所高校选用。
访谈结束后,顺便聊起了家常。先生和蔼可亲,听说我也是闽西老乡,又是北师大学子,一见如故。
根据先生粗略讲过的各个人生阶段,我随手在笔记本上简单列了一个提纲给他,并建议可以先在《光明日报》人物版上刊发通讯,然后再做一部口述史。我负责访谈、录音和整理。
先生愉快地应允了。
于是,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录音长达四五十个小时,最后口述完毕。写通讯的事,却被我以口述史出版之后,通讯自然水到渠成为由,无限期拖延。
后来,在几位帮手的协助下,2014年口述史初稿编成,当时截取了一小部分在北师大校报上发表,大概有几万字,效果很好。
原本想着将口述史作为先生的八十寿辰贺礼,于2016年前后出版。不料2015年6月14日,先生在外出登山途中突然去世。
书稿未出,通讯未成,传主已殁,呼喊无门,遗憾之至,令人心伤。
如今,童先生八十寿辰临近。口述史在童门子弟的帮助下即将出版,通讯也终于完成。
古人说:“事死者,如事生。”先生在那一边,当不会把我视为食言之人吧。
童庆炳大一时在北师大数学楼前留影
2015年5月20日,离生命的谢幕还有25天,童庆炳教授最后一次登上讲台。在电子楼阶梯教室,他应邀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校进行了首场讲座。此情此景,他想起了老师黄药眠,想起了先生为他们上的最后一课。
那一次,黄先生步履蹒跚,坚持自己走到教二楼给研究生上课。平时,这些老派的先生们都一个风格,讲课从不带讲稿,东西都装在脑子里。可这一回,他却带了一个书包,进了教室就从包里掏东西。
童庆炳当时以为先生年纪大了,怕记不住问题带了讲稿。不料,黄药眠却掏出三个药盒,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把童庆炳叫过去说,当左胸疼要不行时,给他吃哪一种药;当另外哪些情况要送医院时,给他吃哪种药。
后来,童庆炳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回顾了这一情节,他感叹:“这最后一课,是他带着牺牲的精神,带着豁出命的精神,来给我们讲的。”
在远古中国,“师”承担着某种神秘的“天命”,因而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殉道”精神。童庆炳也常常追问,自己是否也做到了黄药眠那种“豁出命”的精神状态。
童庆炳的部分作品
而在《教师的生命投入》一文中,童庆炳还提到了黄药眠之外的两位教师。
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卡西尔,德国人,这位汉堡大学原校长因反对纳粹专政而颠沛流离,却始终未离开过教席——
“1945年4月1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卡西尔提问,卡西尔耐心地回答着、回答着,就在这时他猝然而亡,死在学生的怀抱里。”
另一位则是国人熟悉的数学家华罗庚。1985年,75岁高龄的华罗庚赴日本讲学——
“那年6月12日下午4时,他站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讲‘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问题’,精神矍铄,先用汉语讲,后征得与会者的同意,改用英语讲,会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演生动活泼、言简意赅,博得阵阵掌声。他越讲情绪越高,脱下了上装,解下了领带。原定45分钟的讲演时间过去,又补充讲了20分钟。讲完后,听众热烈鼓掌,他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谢意,突然,他倒下,心肌梗塞,不治而亡。”
这些镜头不断盘旋在童庆炳的脑海里。2008年,他得了胃癌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2012年又得了心脏病,安装了支架。此后,每一次应邀登上讲台,童庆炳都幻想着这样一个献身的结局:“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我正在讲课,讲得兴高采烈,讲得神采飞扬,讲得出神入化,而这时候我不行了,我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
这一次,坐在电子楼阶梯教室里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北师大文学院的教师。童庆炳的讲演题目是《如何做“四有”好老师》。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北师大,号召全国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童庆炳深表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四有’是对教师要求的朴实表述和精要概括。”
童庆炳进一步解释:“首先是培养道、传道的问题,其次才是授业解惑。教育要以人为本,所以学校的问题是如何在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要培养好学生,我们首先要从道的层面来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作出榜样。”
确实,童先生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四有”好教师的最好例证。
青苹果
1936年,童庆炳出生在闽西连城山区一个叫莒溪的村庄,那里虽然山清水秀,但贫穷却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后来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二三岁起,童庆炳就开始挑柴、耕田、插秧、施肥、锄草、割稻子、晒谷子,几乎做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极限。
然而,从村子里零零散散搜罗来的书籍中,童庆炳慢慢知道了山外还有一个新世界,知道了在他之前,人类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他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书本播下的种子,让一个追求“五斤米下锅”的小庄稼汉,生发出求学求知的理想。
1952年秋,童庆炳以优异的成绩从连城中学考入龙岩师范,又于1955年从龙岩师范考入了中国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
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可谓群英荟萃,北师大共有6名一级教授,中文系独占三名: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并且流传着中文系“十八罗汉”之说:除了上述三位一级教授外,还有古典文学的谭丕模、刘盼遂、王古鲁、王汝弼、李长之、梁品如,古代汉语的陆宗达、萧璋、叶苍芩,现代文学的叶丁易,外国文学的彭慧,外国文学儿童文学兼攻的穆木天,以及还是副教授的启功、俞敏、陈秋帆。
这些教授几乎都给本科生上过课,童庆炳因此眼界大开。
回忆这些老师时,童庆炳动情地说——
“课上,老师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都会想起他们。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
1958年,童庆炳以优异的表现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沿着众多前辈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行。
童庆炳说:“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我就做好老师就行。”这是他留校之后唯一的理想信念,那一年他23岁。
此后的近六十年间,无论是面对事业的挫折,还是面对职务的诱惑,童庆炳始终没有放弃过讲台,始终没有“把学生给丢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如何成为一名“有理想信念”的好教师。
后来,每逢新生入学,童庆炳都会给文学院师生讲一遍“手握青苹果”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独自到沙漠去冒险,他丢失了全部行李,迷失了道路。他一时慌了,翻遍了所有口袋,终于在一个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苹果。他闻了闻这个青苹果,觉得这是一个水库,是一个粮仓,且无比清香。他握着这青苹果,朝一个方向走去。每每精疲力竭时,他就手握青苹果看一看闻一闻,又向前走,直到第三天黄昏时分,他惊喜地看到了绿树红花,原来已经走出了沙漠。
是的,每个人都应该手握这样一个青苹果,而教师手里的那个,更应该握得紧,永不离手。
溪与石
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家庭生活当中。早年的大家庭生活中,童庆炳受祖母的影响最大。他曾对笔者说——
“祖母身上最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善良,她的善良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我印象中,早些时候,她就对某些方式不能理解,对阶级斗争不能理解。她说,今天我们还是邻居,还是亲戚,怎么能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要去批评、斗争,还有的就枪毙了呢?祖母完全无法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影响极深、影响极大的。‘文革’中,我没有敌人,都是人家批判我。这正是受我祖母的影响。我常常想,按照祖母的逻辑,她就会这么想:今天我们还是同学,还是我的老师或者学生,怎么第二天就变成敌人,就要来斗争了呢?他或者她可能身上有种种矛盾或缺点,但怎么可能会是敌人,要斗争、批判,甚至送到监狱里去或者送去劳改了呢。”
说起曾经的那些运动或斗争,童庆炳很痛心。中国人最常讲的是“忠厚”,做人要厚道,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整人害人。
而从祖母身上,童庆炳把这种观念融入到了血液和秉性之中,化作了信仰之石、价值之基。而这种善良和厚道,也正是所谓“道德情操”的根基。
因为这种善良和厚道的守护,一向看起来柔弱和善的童庆炳,平添了一种难得的刚毅。这种刚毅,常常被人命名为正义感。
“文革”前后,作为“红五类”出身兼老党员的童庆炳,不时被要求去揭露或者整某某老师或学生。为此,他不惜和校领导拍桌子,拒绝整“黑材料”。
因为这种刚毅,童庆炳保护了身边的许多人,他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被同行和同事所敬佩。
尊重别人,容忍乃至欣赏不同风格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包容和大度,童庆炳才一生广交朋友,带领“童家军”闯出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新天地。
童庆炳自己编了一则“小溪和石头的对话”。意思是小溪旁有一块巨石,千百年来岿然不动,永远站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水涨水落,它总是蹲在那里,用冷眼观看着世界的变迁。小溪则流动不止,无论日升日落,无论白天黑夜,用它哗哗的流水和浪花唱着歌。水主动,石主静。水的理想是奔腾向前,石的理想坚定不移。没有理由贬责石头而独尊小溪,也没有理由独尊石头而贬责水流。每个人的健康选择,都有可贵之处。
童庆炳告诫身边的每一位人,我们一生都要学会尊重别人,尽管别人与你那样不同。
聋青蛙
童庆炳的学生蒋原伦教授曾经在《童老师》一文中透露,“童老师的健身秘诀之一是每周登香山一次”。其实,童门早些年的学生几乎都陪老师爬过香山。
在蒋原伦眼中,“他登山的节奏是匀速的、不间断的,且心无旁骛,一步一步地迈向高处。我想,这登山的境界就是童老师为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童庆炳自己则表示,他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
少年的童庆炳,一度辍学在家,每天要走遥远的山路,进山砍柴,然后挑九十斤柴火回家。闽西的山路狭窄陡峭,一边是陡峭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要很小心,不然会掉下去。“特别是雨天,上面下雨,我们头上却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等脚踩上了平地,那么这一天的危险才算结束。”
长大以后,童庆炳明白的第一道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获得成果,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山路挑柴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总是艰苦而又危险。“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
来自农村的童庆炳,从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天赋。上大学时,他甚至有点儿自卑,认为很多地方都比不上那些有基础的好学生。留校工作之后,他也一度被怀疑业务有问题,被迫从教学岗转到行政岗。
然而,就是靠着身上这么一股“挑柴”的劲儿,1963年,童庆炳发表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发表在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上。
在那一组六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中,郭预衡、钟敬文、启功等名家大作赫然在列,而童庆炳与钟敬文的文章篇幅并列最长。
据童庆炳回忆,那时他住在二龙路,从北师大东门坐22路,到西单站下车,但当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红楼梦》的图景,总是坐过站,到了终点站前门,下来回去,发现又坐过了,又要重新上车。
改革开放之后,童庆炳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春天。据百年校庆时北师大中文系编的教师著作论文目录统计,童庆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2年的十多年间,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还有十多种著述。
童庆炳说:“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童门弟子也回忆道:“童老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不读书、不研究、不努力,这也可以看成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他一以贯之的教导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这种心无旁骛和一以贯之,童庆炳常常用“青蛙爬塔”的故事来比喻:一群青蛙要爬一个高塔。他们争先恐后往上爬,过路人看见这群青蛙的愚蠢行为,就大声喊:哎,塔这样高,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于是,有一些青蛙停止了爬塔,退下来了,可还有青蛙继续往上爬。人们又叫喊:哎,你们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赶快下来吧。于是,又有一些青蛙退了下来。经过人们几次喊叫后,几乎所有的青蛙都退下来了。但还有一只青蛙继续往上爬,不管人们怎样喊,那只青蛙都不听。最后,这只青蛙终于爬上塔顶。待这只青蛙从塔顶下来后,人们问它:你凭什么精神爬到塔顶?青蛙摇摇头。原来,这是一只耳朵全聋的青蛙,它根本没有听见人们的喊声,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扰,凭借自己的专注和毅力爬上了顶峰。
童庆炳说:“多少人来劝我,向我喊话,可我没有听见,我是那只聋青蛙。”如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已经根深叶茂,童庆炳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十卷本摞在一起,没有一丝水分,扎实!厚实!
严与慈
很少有人能把“严师”和“慈父”两个词兼具于一身,但童庆炳做到了。
季羡林曾将自己的一个学生推荐到童庆炳门下读博,这个学生私下里向季先生说童庆炳挺厉害的,有些怕他。但季羡林却对童庆炳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能在严师指导下学习是一种福分。
在一篇《宽严相济》的文章中,童庆炳谈及自己三十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宽严须相济,所谓严,就是对学生的学业一定要严格要求,丝毫不能放松。
童庆炳说:“学生来学校,愿意做你的学生,就是希望得到导师的指导,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学生既然想学习到真知识、真能力、真功夫,那么,老师的严格要求就是符合学生愿望的。”
童庆炳讲述过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位学生,他的论文初稿写得很差,完全不能令我满意。我在别的学生面前当众批评他,一直呵斥到他哭了起来,流下了眼泪。当然,他很皮实,没有去寻死觅活,他认真地接受了我的批评,听取了我的指导,最后经过修改的论文很优秀,顺利通过。后来,他把论文拆开,连续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毕业后还当上了某高校的教师,并很快评上了教授。每年春天新茶下来时,我都会收到从南方某地寄来的一盒茶叶。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他寄来的。我从来不把这盒新茶仅仅看成是一盒茶叶,这是我获得的一枚奖章。我把这枚奖章看得比任何奖章都重要,因为这是我执教成功的一个证明。”
然而,当学生遇到困难时,诸如生病、失恋、家人出事、穷得揭不开锅、找不到工作等等,童庆炳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们。
童庆炳曾说过:“是的,我对自己的事情常常是听其自然,很少去争什么。我为自己的事,决不走后门,决不踩领导的门槛,决不托人做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为了学生,为了解决学生的困难,为了帮助学生,我可能去走后门,可能会踩领导的门槛,可能会托人为我的学生办事。”
除了“慈父”,还有谁能这么做呢?
有一位韩国博士生,“非典”期间突然返京要求博士答辩,童庆炳毅然应允。于是,一场在科技楼天井里的特殊答辩产生了,答辩人和答辩委员人人头顶骄阳,戴着厚厚的口罩,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答辩。
严师成人,慈父爱人,仁爱之心,莫过于此。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近六十年的讲台生涯中,童庆炳从来都是站着、走着讲课。
这一次文学院党校的首场讲座,年近80岁的童庆炳依然站着讲到了最后。文学院的新闻报道这样写道:“报告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童先生在报告中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释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童先生的报告真诚又亲切,娓娓道来,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深受感染,场内数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童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四有’好老师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童庆炳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讲演。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童庆炳 教师 培养 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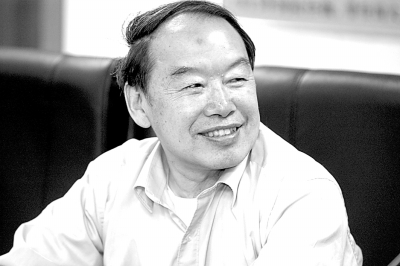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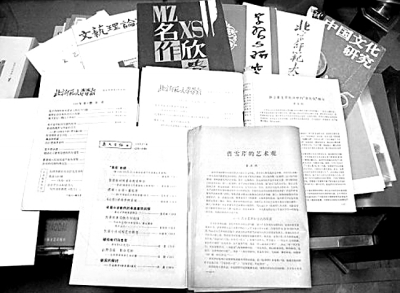


 “超级月亮”现身堪培拉
“超级月亮”现身堪培拉 特朗普发表其执政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特朗普发表其执政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保障春运
保障春运 “欢乐春节”挪威首演闪耀北极光艺术节
“欢乐春节”挪威首演闪耀北极光艺术节 靓丽海冰
靓丽海冰 春运路上有了“列车医生”
春运路上有了“列车医生” 阿富汗官员: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阿富汗官员: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到访武汉大学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到访武汉大学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