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要闻 要闻
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谈24年索赔路 称不索赔是纵容
在纪念馆中,陈列着当年的老照片。
童增,1982年四川大学毕业,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随后掀起国内民间对日索赔浪潮。24年间一直奔走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之路上,被誉为民间对日索赔奠基人。
潘守三回到潘家大院内,回忆往事几度哽咽
潘家峪遗址(网络截图)。
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在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村1400多村民中,有1230人惨死在日军手下。今年7月13日,惨案中部分幸存者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代表来到北京,正式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对日本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人民币60亿元。
前天,京华时报记者对话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详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24年的发展之路。
现在二战受害者活着的已经不多了,可以说民周对H崇赌是中华民族要求H本谢罪赌偿的最后—个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我们应该珍惜。
随着国内环境的宽松,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渐明朗。
1
对日诉讼近30起基本败诉
京华时报:因何机缘,您开始关注民间对日索赔?
童增:1990年4月,我偶然看到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很受启发,我觉得我们也可对日本提出赔偿。
我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发现了很多战争期间日本的罪行。我当时写了一个对日索赔的万言书,但当时没有媒体愿意发表。
1991年我把万言书递交给人大代表,没想到很多代表表示认同,还提了议案。媒体随之跟进,有了社会反响。很多受害人就来找我,我才意识到,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我就想帮他们做点什么,没想到一做就到了现在。
京华时报:那时主要是以什么形式开展活动?
童增:那时只是动员大家将索赔信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单方面要求对方进行赔偿,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没什么进展。
这种情况一直到1994年才有转机。当时有日本的律师找到我,说希望代理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案件。于是我们委托他们在日本打官司,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日本200多名律师自己筹款帮中国人打官司,还有10万日本人签名支持我们,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
京华时报:索赔情况如何?
童增:这些年我们在日本提起了近30起诉讼,基本都是败诉,无一人拿到赔偿。今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起诉案会在日本宣判,根据经验也会败诉。
2
不索赔就是纵容于国不利
京华时报:对日索赔为什么这么难?
童增:日方理由主要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战争赔偿,包含个人赔偿。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回应对日索赔诉讼案,认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弃,在法律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但日本的这种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从未放弃个人赔偿。
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多位领导人对此已多次阐明立场。
2007年,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声明》做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京华时报:屡败屡诉,坚持的意义何在?
童增:我们越是友好、忍让,越是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日方也趁机开始美化战争,扭曲历史。
暴行不提起到法庭,不要求日本索赔,那我们就是纵容日本篡改历史、不承担责任,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的起诉,一方面能够帮日本恢复记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胜诉,也会为二战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也算对国际尽了一个义务。
受害人是拿着法律的武器到法院去申诉,从长远来看,这个中日之间的障碍(指对日索赔)解决了,会更有利于双方友好。
3
在中国提起诉讼
有法可依
京华时报:潘家峪惨案的受害者,此时提起诉讼有何意义?
童增:这应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里程碑式的发展,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劳工、慰安妇之类的个案,而潘家峪案有1000多名受害者,现在幸存者们集体起诉日本,这是首次。
京华时报:潘家峪对日索赔诉讼在国内起诉,您预期如何?
童增:日本政府在对待侵华历史上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法庭上很难获得公正的判决。而且诉讼在日本开庭,受害人过去非常不方便。
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实际上从2005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有所倡导。今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已经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也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战争罪是反人类的罪行,根据国际法,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起诉。应该说,在国内提起索赔诉讼是完全可行的,也有国际法可依。
在索赔方面,不论是政府索赔还是民间索赔,有很多国际范例。比如韩国当时也放弃了各种战争赔偿,但现在有受害者在韩国国内提起诉讼,韩国高等法院已经判胜诉了。
不过,这对于我国的法院来说,可能仍是一个新的课题。
4
受害人年事已高
时间紧迫
京华时报:您认为未来对日索赔的前景如何?
童增: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近些年来,我可以感觉到民间对日索赔开展得越来越顺利。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相信对于民间对日索赔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但是我们也有紧迫感,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一打官司就是20年。上世纪90年代给我写信的受害人,很多已经去世了。现在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八九十岁,他们等不了了。虽然他们都是自愿站出来,但是出来作证对他们都是二次伤害。
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应该尽快能够有一个结果。如果这些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谢罪,对他们将是莫大的安慰。
因此我们也希望法院尽快立案、审理、判决,社会多关注这些老人,从道义上、经济上、精神上给予他们一些关爱。
京华时报:您如何看待这么多年的民间对日索赔工作?
童增:这些伤害只能靠我们向全世界去诉说,要靠人家来帮我们去发掘一些材料是不可能的,现在还有很多西方国家不了解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政府公布档案资料是一方面,但由众多的受害者来揭露暴行,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有活的证人,把他们受到的暴行经历向全世界诉说,这个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民间对日索赔是正义的事情,也是顺应民心的。只要我们坚持,总有一天可以做成。
□讲述
每人拎一条腿,活活将孩子撕开
“1400多村民,1230人惨死在日军手下”
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坐落着一个被誉为“小吐鲁番”的美丽村庄。
7月15日,京华时报记者来到河北潘家峪村时,整个村庄显得宁静、安详。但村内的潘家大院遗址,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73年前的屠村惨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潘家峪村1400多村民,就有1230人惨死在日军手下。
“两日本人抓起孩子,提着腿活活把人撕开”
那一年潘守利12岁,被压在潘家大院中一个猪圈的死人堆里,逃过一劫。
忆及当年,老人一声重重长叹,还未开言,便已哽咽泪流,“想起那些就难受,特别难受……”
1941年1月25日,本是筹备过年的日子,不料日军从四面八方将潘家峪围堵,挨家挨户用刺刀将村民圈到了村口的大坑中。众多村民逃跑,日军随后又将大家逼进了潘家大院内。
惨案的另一名幸存者潘善增,当年6岁。他记得,村民们进入大院后,门就关了,日本兵开始往院里开枪,扔手榴弹,“大家哭喊着到处跑,找地方躲,有的人冲到门口求情,被日本人一刀砍断脖子。”
潘善增是被母亲塞到厕所坑洞里才得以活命。除了头部没被压着,身上层层地压着死去的村民。
当年13岁的幸存者潘守三也侥幸逃过一劫。潘守三亲眼看到,一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孩子,奔逃中被两个日本人抓住,他们提着腿活活把孩子撕开。还有日本兵从抱着娃儿的妇女手中把孩子抢走,摔在石头堆砌的院墙上……最后,日军端着刺刀在死人堆里找活人,看到还有口气的就补上一刀。如此三趟,方才离去。
“27名惨案幸存者,年龄最小者已经77岁”
潘家大院和村口的大坑作为惨案遗址保留至今。直到现在,潘守利老人都不敢进村口的陵园,一到陵园门口,他就想起那些惨死的人,忍不住浑身发抖。
1999年,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建成,潘家峪村也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年7月13日,潘家峪村以全村的名义,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索赔金额为60亿元。
66岁的村民、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潘瑞申说,2002年,大惨案的幸存者还有38人,12年过去,只剩下27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已经77岁。
“再过几年,能说话、能出来作证的人会越来越少。”潘瑞申说,但愿通过诉讼,能给这些老人一个交代,能让世界认清日本的战争罪行,“日本的罪,永远也抹杀不了。血海深仇,一定要讨个公道。”
文/京华时报记者陈荞 实习生杨艳萍 图/京华时报记者王苡萱
编辑:曾珂
关键词:民间对日索赔 对日索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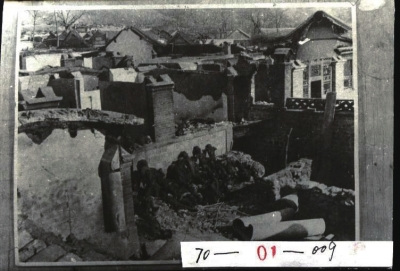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中国制造助力孟加拉国首条河底隧道项目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澳大利亚猪肉产业协会官员看好进博会机遇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约117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伊朗外长扎里夫宣布辞职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中国南极中山站迎来建站30周年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联合国特使赴也门斡旋荷台达撤军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长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1年监禁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开夜场举办“灯会”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