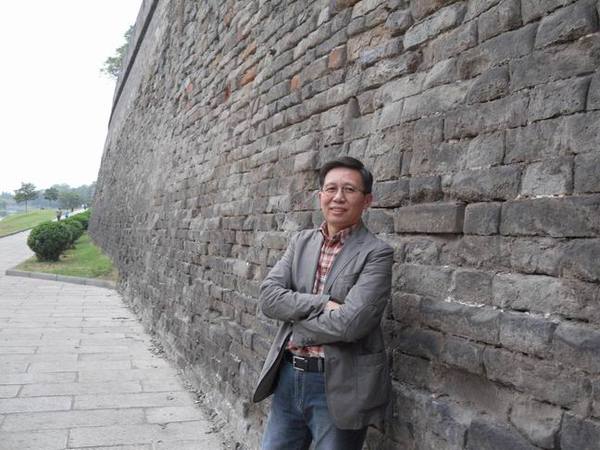首页>人物·生活>秀·风采秀·风采
陈应松:作家首先要与人民同行,才能谈责任感使命感
陈应松
阅读提示:
■所谓底层,就是这类人,他们的一生,从某种角度说,跟蚂蚁的一生没有两样,跟一片枝叶的一生没有两样。
■我熟悉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充满感情,我不写他们,我就没有写作素材。
■好的读者跟好的作家一样,非常稀少。在当今社会,不读书的人太多,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喜欢经典,喜欢读一些深刻的东西。
日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湖北省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应松的《滚钩》获得中篇小说奖。
《滚钩》是陈应松2014年的作品,该小说取材于发生在湖北的一个真实事件,因塑造了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底层人物形象,甫一发表就受到社会的关注与好评。
陈应松是一位拥有独特创作风格与人文思考的作家。他擅长描写底层人物,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观照思考社会现实,他的这一特点不仅仅体现在《滚钩》之中,之前的《马嘶岭血案》、《猎人峰》、《到天边收割》、《失语的村庄》等作品莫不如此。在《滚钩》获奖之际,本报记者就文学与生活、当代作家应怎样创作出“有营养”的作品等话题邀请陈应松进行了专访。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创作
文化周刊:《滚钩》源自几年前发生在湖北的一则“挟尸要价”的新闻事件,您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把握其新闻“真实”与创作“虚构”之间的关系的?
陈应松:这个新闻事件太令人难以忘怀了,简直就是为作家准备的。但我的小说《滚钩》与这个事件本身没多大关系,我只是借用了这个故事的壳,或者说取材于这个事件,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
小说需要真实,但这个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不同的,它服从于艺术表达和作家个人思考的真实,是文学必须达到的一种真实感觉。虚构文学作家与报告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创作的时候,我最先考虑的是要塑造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这需要我在我的记忆仓库里搜寻———我要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全新的角色,要有他的独特性,更要有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我说,这与真实事件本身没多大关联,我是要在我塑造的人物身上挖掘更深刻的意义,那么这时候虚构可以说就是一切了。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虚构比真实的生活有更大的空间。就我本身而言,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我更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变形,所以,在文学创作中,虚构是我所热衷的。
文化周刊:您在《滚钩》中塑造了渔民“成骑麻”这一主人公人物形象,并从他的视角去审视、推动、贯穿整个情节的发展,您想通过他表达怎样的情愫?
陈应松:“成骑麻”这个名字我现在都不记得是怎么想出来的,有点儿怪。我用这个老渔民作为小说《滚钩》的主人公,以他作为叙述的视角,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写长江,离不开船工、渔民,成骑麻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物。一个渔民成为捞尸工也是不容易的,有时是为时代和生活所迫。渔民嘛,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我们也应该理解和同情他们。以一个老渔民的眼光来审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应该是有意思的。成骑麻这个渔民、船工出身的捞尸人的悲剧是我想要表达的,我就是想塑造这样一个一辈子辛勤劳作、最后反而被人们唾弃的人物形象,时代的荒唐性就在这里。通过一个渔民的命运的悖论,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一些令人厌恶的地方,等等。
文化周刊:有的学者将《滚钩》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做类比,认为您在创作中受到了海明威作品的影响,是这样吗?
陈应松:有一点影响,但不大。我写过老船工的故事,还不止一个,我受我自己的影响可能更大些。《滚钩》显然是长江上发生的故事,之前是一个他人从未涉猎过的题材,在中外小说中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故事,是我的典型风格。
“我所写的底层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文化周刊:我阅读了您的一些随笔和演讲稿,看到您对神农架远离城市喧嚣、贴近自然的向往与赞誉,但同时您也创作了暴露神农架地方“丑恶”或“愚昧”一面的小说。有学者评价您的“神农架系列”是通过自然、人文风情的描绘,寻找人类“救赎”之路,从而建立呵护自然的人伦规范和生命价值。“神农架系列”的创作初衷是这样吗?
陈应松:有关神农架,刚开始我没想写什么系列,因为在神农架挂职,得到的生活素材太多了,写了几年,回头一看,有那么多。后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提出“神农架系列”的说法,这个说法传了出去,逐渐被文坛所接受。
保护一座山就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世界的原始状态,就是保护我们人类最早的家园,保护我们自己免遭毁灭。我想真实地写我心中的神农架,特别是在那里艰难生活的人们。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定有大量的感动,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最值得我尊重。我希望许多丢失的东西都能在那儿找得到。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和寄托。我走进神农架的大山、森林,的确渴望探寻自己幸福的另一个源头,相信这里的美胜过他处,这里的传统能够拯救当今社会。但后来发现我太自不量力了,我发现我依然是一个俗人……我就写几篇小说而已,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就行了。在神农架,人直接与大自然发生关系。远离城市这个欲望的世界,生态环境就在你的眼前,这个环境真的非常脆弱,也非常险恶,我们要有忧虑之心。
我没有去刻意表现神农架的丑恶和愚昧,只是写了某种山区的原始状态,但我依然是怀着真实表现和歌颂自然的心态写的。我可能比别人写得“残酷”一点,我的写作方式是如此。
文化周刊:在谈到写作“远与近”的问题时,您说自己是属于写“远”的作家。在选材上,为何钟情于离武汉很远的神农架?
陈应松:我不爱凑热闹,我比较安静,我虽然谋生的单位在城市里,但写作这个职业并不适合待在城市里,不是大家天天扎堆就能写出好东西来的。写作是要到边边角角去的一项营生。我生性又比较“野”,就盼着有机会能往山里钻,往远方走。现在不是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吗?好,那我就深入到湖北省最远的地方——神农架。怎样生活都是一辈子,我是一个作家,想按照自己的内心“冲动生活”,就算什么也写不出来,但生活在神农架,这本身就是多么惬意的事!住在森林里多有趣呀,简直可以变成童话中的人物。
文化周刊:十几年如一日地在神农架采风、调研甚至挂职,并与当地农户融合在一起,您曾说:“这些年虽在城市,却尽量躲避城市,我的乡土意识是在城市的生活煎熬,它的冷漠、亢奋、凌乱、无情,在浓浓的终年不散的雾霾中被唤醒。”是什么支持您一直注视现实、注视底层、关注乡村?
陈应松:我真的只是喜欢神农架,至于神农架喜不喜欢我,我不管。我一个平原上出生的人,对山有永远用不完的好奇心。至于我的作品出现的你说的这些特质,还是我一以贯之坚持的写作态度和理想。作家生活在这个时空,要直面这个时空的现实。脱离了现实,作品能深刻得起来吗?没有现实忧患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有的作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有的作家却一辈子在胡编乱造,连文学是什么都没搞明白。现在,特别是有些网络作家,我认为他们只能叫商业写手,离真正的文学和真正的作家还很远。一个作家,只有路走正了,作品才有分量。
我之所以这样写,写成如今的样子是有缘由的。我自己就是个底层人,各式各样的工作我都干过,各式各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我出身于普通家庭,我家父母和两边的亲戚,翻出八代也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样不进入文字记载的人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所谓底层,就是这类人,他们的一生,从某种角度说,确如蚂蚁的一生,跟一片枝叶的一生没有两样。我熟悉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充满感情,我不写他们,我就没有写作素材。我所写的底层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陈应松 作家 责任感 使命感 《滚钩》 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