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人物·生活>记·工作记·工作
黄顺基:道法自然 渐臻佳境
哲学之思
1957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逻辑学教研室的王方名和黄顺基到中南海,要整理好衣装。听闻电话打给了时任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说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接见时的情景令黄顺基终生难忘。“到了新华门,由门警通话,然后引我们沿中南海步行到颐年堂,田家英(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和我们谈话不久,便见主席从后庭迈步走进厅堂,他后面紧跟着周谷城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主席握手。”黄顺基回忆道。
“这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的观点相同嘛!您有知音呀。今天约大家来谈谈。”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
落座不久,又陆续来了一些哲学与逻辑学界及学术界的前辈,其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黄顺基万万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与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后来,黄顺基才知道,这件事并非偶然。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就在这时,逻辑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方代表苏联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学科,它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说“同就是同,同不可能是异”;另一方则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同一律是指在思维与论述过程中应保持对象的同一性。与此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
王方名和黄顺基对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关文章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凑巧的是,他们的意见与周谷城不谋而合。
《教学与研究》面向全国发行,毛泽东非常重视,在百忙之中经常深夜阅读上面刊载的文章,以了解国内的思想理论动态。国内这次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学习苏联问题的继续,因此毛泽东力主邀请争论中的有关人士到中南海座谈。
这次会见,毛泽东主要谈的是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
接着,毛主席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然后,他转向周谷城,“你的观点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座谈的气氛轻松而愉快。金岳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被公认为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创始人。毛泽东希望金岳霖能够推动国内逻辑学的研究工作。费孝通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早春的天气》一文。毛泽东对他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插话道:“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邀请大家一起用餐。黄顺基紧挨着主席入座,田家英坐在主席左边。主席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当加上杂粮的米饭端上来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这是金(黄色小米)银(白色大米)八宝(各种豆)饭。”
服务员斟上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在黄顺基看来,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声称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这是何苦来哉?!
坐下来后,毛泽东转过头来给黄顺基夹菜,并亲切地询问他的年纪、哲学系主任是谁。当听说系主任是何思敬时,毛泽东说:“哦!我们在延安认识。”
饭后,大家坐下来接着谈。黄顺基记得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几位学者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是胡绳(或者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动物还是有思维的。”
毛主席谈兴甚浓,从上午10点钟起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意。黄顺基等人怕主席过于劳累,于是起身告辞。“主席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枝叶繁茂的桂树说:‘八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回到家里,黄顺基兴奋得彻夜难眠——“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学术界前辈相识,如此殊荣真得感谢《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理论界‘一面倒’的情况下,它竟然敢于发表与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意见,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己任,谈何容易!”黄顺基不禁感慨道。
此后,借由早年同《教学与研究》结下的不解之缘,黄顺基再接再厉,思维不止则笔耕不辍,在该刊物上先后发文20多篇,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
书信之缘
虽然钱学森与黄顺基的专业领域不同,从事的工作性质也不同,但二人却因“英雄所见略同”而有着长达10年的书信交往,其情谊鲜为人知。
二人的相识,还要从1986年黄顺基组织编写的《大杠杆》一书出版说起。“当时社会上反响强烈,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述评给予高度赞扬。我没有想到,钱老也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写信来表示祝贺,他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
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刘奇曾经与钱学森同住一个大院。“一次散步时碰见,钱老问我是否看过《大杠杆》,并郑重地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要好好阅读,可见这本书给钱老的印象很深。”刘奇说。
1996年在获悉《大杠杆》获奖后,钱学森又很快给黄顺基寄来信件:“我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恭贺尊作《大杠杆》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4年,黄顺基写了一篇文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投到《人民日报》。当时学术界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不同意这个观点,因而黄顺基的这篇文章很可能发表不出来。“《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卢继传读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他出了一个点子——把文章的题目从肯定的语气改为商榷的语气,以《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为题发表。”黄顺基说。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刊发出来,黄顺基将其寄送给钱学森。关于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95年内,钱学森先后给黄顺基回复了三封信。
2月26日,钱学森在回信中说:“您前次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因此我已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此事。”
5月29日,钱学森又来信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26日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
9月3日的来信内容则是:“我从《哲学动态》的专访稿中才知道您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属自然科学,所以您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当然比不学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胜一筹。您现在看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比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要高明,道理就在于您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技术。”
同年9月11日,钱学森在密切关注新产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余,给黄顺基寄来美刊《科学美国人》,要他注意信息技术的发展。“钱老认为,信息技术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建议我组织力量探讨‘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
对此,黄顺基回信道:“‘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题目非常好,这是一个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课题。如果说第三次产业革命把落后的欧洲推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为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物质技术与思想基础,那么,您所提到的、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正确的设计、指导与协调的条件下,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迅猛前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新的篇章。”
黄顺基认为,如此重要的课题一定要请钱学森亲自挂帅,因为“以钱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方能驾驭”。
然而,钱学森却在黄顺基的回信上签注:“我只能当顾问,不挂帅”,并请自己领导的课题组成员汪成为院士、戴汝为院士、王寿云秘书长、于景元所长、涂元季教授、钱学敏教授考虑此事。
1996年9月16日,“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人事部、交通部等20多个单位的3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前,课题已被批准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重点研究项目”,由钱学森任顾问、黄顺基任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负责组织实施。此后的研究成果有:《信息革命在中国》(1998年)、《现代信息技术基础知识》(2001年)。
“回想起来,我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成果,与钱老对我的关怀、帮助与指导是分不开的。”对此,黄顺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编辑:邢贺扬
关键词: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 管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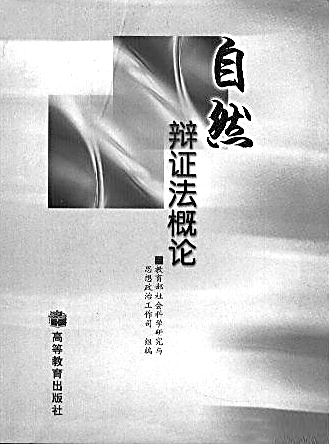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贵阳机场冬日为客机除冰 保证飞行安全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保加利亚古城欢庆“中国年”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河北塞罕坝出现日晕景观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尼尼斯托高票连任芬兰总统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第30届非盟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开幕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保加利亚举办国际面具节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叙政府代表表示反对由美国等五国提出的和解方案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洪都拉斯首位连任总统宣誓就职
 法蒂玛·马合木提
法蒂玛·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胜阻
辜胜阻 聂震宁
聂震宁 钱学明
钱学明 孟青录
孟青录 郭晋云
郭晋云 许进
许进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吕凤鼎
吕凤鼎 贺铿
贺铿 金曼
金曼 黄维义
黄维义 关牧村
关牧村 陈华
陈华 陈景秋
陈景秋 秦百兰
秦百兰 张自立
张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兰
李兰 房兴耀
房兴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义孙
曹义孙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国枢
詹国枢 朱永新
朱永新 张晓梅
张晓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张连起
张连起 龙墨
龙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巩汉林
巩汉林 李胜素
李胜素 施杰
施杰 王亚非
王亚非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姚爱兴
姚爱兴 贾宝兰
贾宝兰 谢卫
谢卫 汤素兰
汤素兰 黄信阳
黄信阳 张其成
张其成 潘鲁生
潘鲁生 冯丹藜
冯丹藜 艾克拜尔·米吉提
艾克拜尔·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学诚法师
学诚法师 宗立成
宗立成 梁凤仪
梁凤仪 施 杰
施 杰 张晓梅
张晓梅


